四、上杭黄坑二十七郎开基地四三郎裔孙谱序系列
【编者按】以下五篇老谱序均为黄坑四三郎房裔孙所撰。该房第一个写谱人丘昂在1504年作序时,不知二十七郎父母是谁,仅“取祖叔讳茂敷笔记,称继纶之迹验是为裔。”从一世祖二十七郎公开始写起。1684年,该村之麟公修谱,“惟立丘公八郎为始祖,二十七郎为一世祖。”1748年,生于黄坑,长于江西龙泉的志高公回乡修谱,擅自篡改了1504年丘昂序。1875年该村臣飏公修谱,“概尊八郎公为始祖,二十七郎公为一世祖。群皆帖服,无纤微可议。”1889年国荣公撰序,云:“惟上祖源流一则,前人一概未述,……查得继龙公之名字,诸先辈俱未说及,只有八郎公。万历二年筑造梅花落地,迎魂安葬,碑书‘八郎公之墓’。崇祯六年创建杭祠,立神主:始祖八郎公。至咸丰四年换过神主,则写始祖‘继龙公’。八月秋祭,镇平蕉生等来杭,痛责易名之错。”事实上,上杭二十七郎一脉的黄坑老谱、扶阳老谱从来没有所谓继龙、伯七郎、三五郎之记载。这就是黄坑历届修谱对上祖源流世系的真实反映。
诸如广东翁源认属葬于江南凹头寨的仁义公为四三郎之裔;上杭太拔赖罗坑宗亲认属罗坑开基的百三郎(葬太拔)为四三郎之子;上杭横冈河田山宗亲认属其三八郎为四三郎之裔;广东梅州江南中心坝宗亲认属成斋为四三郎裔,……等等均应予考证。
丘氏族谱序
夫宗者,绪也,所以继世而原其本也。何也?苟无其本则其末槁矣,又岂有发荣乎?譬如木也,培其根而枝叶畅茂;水也,浚其源而流派自长。人之有祖也,不绪其宗,子孙奚由而生乎?人物虽殊,而其理则一。
今考之一世祖二十七郎,世居宁化石壁,时值宋末,彼地扰攘,人民鼎沸。因同两兄携母带子移于上杭而居焉。自二十七郎而生三五郎,由三五郎而生四一郎,次曰四三郎,三曰四七郎,同居黄坑。四曰四九郎,移居扶阳。五曰四十四郎,移居来苏,由此一脉而分。盖始于高,由高而曾,由曾而祖,由祖而父,由父而身,由身而至于子,由子至于孙,等乎百世之上,俟乎百世之下,其所以继者,无殊也。由是由其端绪而寻绎之,自古及今三百余年,或出生仕于王朝,或创造于他邦,子孙繁衍几近万指,甚宗绪有乖,或五六世之前,或八九世之后,茫无考证,相睨则途人者有矣!今嗣孙讳昂,取祖叔讳茂敷笔留于祖,称继纶之迹验是为裔,以昭后世也。苟或不绪而辑之,则图籍次序坠地矣,安能光前裕后乎?故必世世子孙,济济相继无废坠焉耳。凡遇春秋祭祀,始祖考妣是继是承,席洪庥于既设而得以亲其亲,俾昭穆秩然有条,尊卑井然有序,族门一体,荷先世之遗风,阐扬扶植同归于万世。此非沽名钓誉为于房族也,是乃一遵始祖之贻派耳!昔孔子有言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信乎其然,则后之相继而述者鉴之。
大明弘治十七年(1504)孟春月
嗣孙讳 昂 撰族谱序
河南郡邱氏族谱序
夫宗者,绪也,所以继世而原其本也。何也?苟无其本则末槁矣,又岂有发荣乎?譬如木也,培其根而枝叶畅茂;譬如水也,浚其源而流自长,人之有祖也,不绪其宗,则子孙奚由而生乎?人物虽殊,而理则一。故在盛世,祖宗积德而子孙繁衍,盖有由矣。
粤稽始祖考邱公八郎,祖妣韩氏八娘,生三子:长惟长,次惟福,三惟禄,世居宁化石壁。时值宋末,彼地扰攘,人民鼎沸。一世祖惟禄公二十七郎,三兄弟同母韩氏,移居上杭胜运、来苏黄坑而居焉。自二十七郎而生三五郎。由三五郎而生四一郎,乏嗣;次曰四三郎;三曰四七郎,同居来苏之黄坑;四曰四九郎,居胜运之扶阳;五曰四四郎,居来苏之林塘。皆由一脉而出,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其所以继者咸无异也。
由是绪,黄坑祖邱四三郎生三子:长曰六九郎,次曰六七郎,三曰六十郎。六九郎分派黄坑,居上村;六七郎分派黄坑,居下村;六十郎分派居广东镇平县员子山白泥湖。于此抽其端绪而涵泳之,亘古迄今三百余年矣。或发荣于当代,或创业于他州,探本穷源,如是而已。
昂恐宗绪不详,则五六世之前,或八九世之后,恍惚迷离,有相睨如途人者矣。于是取叔祖太茂公笔记,称一世祖惟禄公至九世继纶公之事实,详为考复,以昭后世。苟不绪而辑之,则图籍次序坠地矣,焉能显宗祖而耀前代乎?故必历世子孙咸在,可作可述,济济相承,无废坠耳。
凡遇春秋祭祀,始祖考妣,是继是承,席洪庥于既没,而得以亲其亲,俾昭穆秩然有条,尊卑井然有序,而不失其真,非他人可比也。厥后子孙,一体荷先世之宗风,阐扬扶植,同归于万世,此非沽名钓誉于宗族也,是乃一遵始祖之贻派耳。孔子曰:虽百世可知也。信夫!后之相继而述者,其鉴之。
时 大明弘治十七年(1504)孟春月
岁进士 任广东和平县知县 十一世嗣孙 邱昂 谨序
大清乾隆十三年(1748)丙辰
恩科举人 十九世嗣孙 志高 敬述
【注】以上两篇谱序均署名昂公1504年撰。上一篇来源于早年由上杭黄坑外迁的广西平南大坡镇大寮村丘氏先祖保存的《丘氏族谱·谱序》。因广西距离福建上杭太远,未曾受到统宗统系之风的影响,序中内容可信度较高。下一篇来源于浙江云和县大源乡四九郎公一系《邱氏宗谱》。因云和宗亲曾在清代修谱时去过上杭,遂将经志高公改了的丘昂公谱序带回云和。
丘昂,黄坑人,二十七郎十一世孙,曾任广东和平县知县。志高,字象乾,黄坑人。清乾隆元年丙辰(1736)由江西龙泉籍中式江西榜恩科举人,历任四川铜梁等县知县。
广西平南谱:只载一世祖二十七郎及二兄并母亲,却没有二十七郎与父母及二兄之名。广西平南谱未载六十郎分派广东镇平县员子山白泥湖。昂公写谱时镇平尚未建县。
河南邱氏族谱原序
予读史,历观司马子长世家诸记,因思古人行藏出处、离合聚散、姓氏名字,非有以记之,虽美弗彰,虽彰弗传。不惟后之人弗传,即其子若孙,年远事久,且有茫然失怀其祖、其父、生平之履历行状,况于一家伯叔亚旅之端委乎?又况于支分派远,与夫婚聚外氏之繁杂者乎?
予于是有感世之巨族大姓,法子长之记以谱其一氏之源流者,散则聚之,离则合之,事则叙之,而派则图之。诚有如苏公所谓:某也善,可以劝;某也不善,可以惩。大哉谱乎!信有裨于世教,不可不仿而作矣。不作则本源何以溯?支派何以别?宗庶何以明?昭穆何以辨?势必至尊卑有所不知分,世代远近有所不知考,殊居异处,行实名字有所不相通,甚且适然遇之,恝然途人视之,有不能知其初同为一人者,谱之作岂细故哉?
是以龙门子有言:“三世不修谱牒,谓之不孝,君子慎之。”蒲阳朱氏文霆亦曰:“族之有谱,所以明派系之别,而本其生之初也。”审是言以知:有谱者则花树常家,往来时睦族;会无谱者,若崇韬贵显误认错拜子仪。由此观之,则族之宜谱,故理之在必叙,而谱之当叙,亦事之所务详。然与其附会故老传闻而述空言,孰若追寻现存之旧迹而纪实绪述?恐沿讹以滋疑,纪绪乃有据而可信。
今稽予族丘氏,溯厥来源,自出太公望,封于营丘,其子孙乃因地以为姓。按之《氏族大全》,邱姓实本于此。迨至后裔蕃衍于河南,遂乃又因之以名郡。爰及东晋五胡乱,复渡江而西,由江西南入闽,散处于宁化石壁,所谓丘家坊者居焉。予祖丘公八郎乃其后也。公娶韩氏妣,生三子:长曰惟长、次曰惟福、三曰惟禄,即二十七郎。时皆长,值公俟命先弃世,乃葬于宁化之紫林滩。继宋末,世又大乱,而宁地遭兵燹,凤鹤尤甚,乡人恐,族众各逃,而禄公同二兄,携其母,挟全家,流移于杭之南坑湖洋里税驾住焉。惟长公遂世居此,今全乡皆其遗裔也。而惟福公则又移于胜运之黄沙埔,有所谓丘存儒、丘存宪、丘存烈,一时叔侄七庠士者即其后,因袭里乃改姓为黄,犹一房流于大埔虎头砂,时亦有来拜祖者。
予祖惟禄公,其始由南坑,旋徙于扶阳之上坪,继又更迁,乃卜于黄坑乡焉。生一子曰三五郎,三五郎公生五子:长曰四一郎,早丧无嗣,附葬于父坟之张天海螺形;次曰四三郎,即予房之三世祖也,承旧基,仍黄坑之鳌头;三曰四七郎,分居黄坑之磜下,随移居广;四曰四九郎,复移居于扶阳之畲里,是为扶阳三世祖;五曰四十四郎,其后居来苏之林塘,是又为来苏房之三世祖。此其上祖分房之大略也。
若乃更推溯而上之,则又有七子流传之派:一曰伯一郎、二曰伯二郎、三曰伯三郎、四曰伯四郎、五曰伯五郎,伯六郎、伯七郎、伯八郎、伯九郎、伯十郎。其伯三、伯六、伯八皆早逝,唯七子盛传。其所谓伯七郎公者,是云予等远祖也。但从来相传如此,未曾有庐墓之可考。观之欧阳子谓谱,当从其可知者,今亦叙其近而可述者,置其年远世湮而不可稽者,可也。故今邑中建祠,唯立丘公八郎与韩氏八娘为始祖,亦从近可知之意也。
第祠可以分房自建之,而谱则必合众房以共叙之。庶无遗系漏派,如月散万川印归一照。所谓溯本源者在此,别支派者在此,明宗庶、辨昭穆者,亦无不在此。而图谱之举岂苟然哉?然谱牒则合以图之,而序世则又分长、禄二公自为一世者何欤?此乃本乎理,而由于礼也。夫一之者,所以推肇迁之功,而著开宗之德也,明重礼,故然也。而韩氏祖妣与子同来,何又谓之始?盖始者由其子以追称之也。《礼》曰:“夫死从子”。此乃礼之昭昭,历千百世圣人复起而不能易者。所以,与迎魂镌碑之夫丘公八郎同号为始也。
夫迎魂镌碑,后人追远之事,非真开基迁来之祖,是以称之谓始,岂有夫称始而妻不称始者乎?明此理者,其惟昔之明经讳昂,孝廉讳梦鲤者。二公皆以道学闻,其序并以惟禄公为一世者。岂非有见于义之至妥,理之至当,事之至确,而漫为浪序哉?是故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凡叙谱者,须从正世始。若二公者,可谓知礼而能正世之名矣。然于序世之大义则既昭,其搜流索派,尚未见图其分而辑其全也。得无采之而或犹有未详欤?考之而或犹有未遍欤?胡为仅仅一序,存其志而不终其事欤?
迄于今,嗣英济济,人文蔚兴。读书者,可谓际其盛矣;怀才者,可谓储其多矣。然一言及谱事,未有不攒眉退却者,非序谱之难,而图谱之难也;非图上祖之谱之难,而图分流别派之谱之难也。予也不肖,辱蒙族众谬推任宗祠执掌。耄矣无能,上何以酬祖德?下何以谢群推?碌碌庸庸,徒为守册,清夜扪心,宁不自愧?因思尚有族谱一事未叙,苟或能摭拾万一,亦聊可以塞责。
于是,日夜焦怀,惟图谱是虑。又恐代愈远而事愈湮,文献无凭,考稽莫据,遂乃遍咨细访,积累居诸,汇成一册,庶籍是以上报祖德,下慰群情,纵鄙词陋议,见笑大方,所不顾也。敢曰效苏氏劝惩之意,以启人心之孝悌,使之尊卑有所分,世代近远有所考,殊居异处、行实名字有所通。若子长者记其事,以传于后哉?亦惟待后之贤达有志于斯谱者,为草创之一助云。
时 大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岁次甲子仲夏月
十六世 八十寿裔孙 讳之麟 谨序
【注】此谱序原载于二十七郎开基地上杭下都黄坑《丘氏六七郎公族谱》。序作者之麟,字瑞元(1595—1694),是二十七郎公派下六七郎公裔,世居黄坑,寿高99岁。1684年之麟公作此序时已年高八十。
河南邱氏增修族谱序
从来族谱开先之祖,则必从其确有可凭者而首书之。《记》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夫家之有宗族,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支,而要其本源则一。故祖必有所自,始溯其所自,二十七郎邱公惟禄,实迁来黄坑肇基之祖焉。基址有足征,庐墓有可据,遐迩孙支瓜绵椒衍,实本乎此。
先达辈,岁进士、任广东和平县事昂公;举人、知山西榆次县事梦鲤公;九十四寿庠生润谷公;九十九寿庠生之麟公等,礼义明悉,研究精深,概尊八郎公为始祖,二十七郎公为一世祖。群皆帖服,并无纤微可议。故杭城南门建祠,神主及列祖坟墓,皆书始祖八郎公,一世祖惟禄公为序。即或仍旧基,或移异处,别派分支,莫不从此而推焉。树议既精,书写自当历千百世,悉依此为序,莫或易之者。
迨乾隆十年,庠生一炳公等酌议三大房合刻五代。以下服属既分,各自分刻支派。迄于今近百三十年,且屡遭兵燹,风霜剥蚀,帙数间或散失。此谱若不增修,将见年愈远事愈湮,文献无征,考稽莫当。于是众裔酌议,将五世祖六七郎公一脉修刻,由五世祖上及始祖,下及二十六世,旧者因新者益成图,汇集付梓精刊。俾得支派虽分,举目了然,要归于一。
非敢谓能尊祖敬宗也。诚以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不过谨述事由弁之谱首。庶后之人,确有可据,永无差忒焉尔。自此以往继起,有贤达则跂予望之。
时 大清光绪元年(1875)乙亥冬仲 之吉
廿四世嗣裔 邑庠生 讳臣飏 敬撰
【注】此序来源于二十七郎公开基地福建上杭下都黄坑1875年编《邱氏六七郎公族谱》木刻版原件,该谱保存完好。序作者臣飏,号弼廷,世居福建上杭下都黄坑,系二十七郎公派下六七郎公裔孙。他说:“先达辈,岁进士、任广东和平县事昂公;举人、知山西榆次县事梦鲤公;九十四寿庠生润谷公;九十九寿庠生之麟公等,礼义明悉,研究精深,概尊八郎公为始祖,二十七郎公为一世祖。群皆帖服,并无纤微可议。故杭城南门建祠,神主及列祖坟墓,皆书始祖八郎公,一世祖惟禄公为序,即或仍旧基,或移异处,别派分支,莫不从此而推焉。树议既精,书写自当历千百世,悉依此为序,莫或易之者。”
上杭黄坑增修源流序
前贤诸公,各题有序,已妥已悉,何待再言?惟上祖源流一则,前人一概未述,至今何敢述焉。因各乡族谱,俱已溯及,今欲随其款式,聊刊卷首,故不入图,是以不信其实据也。
盖邱氏源流,出自太公望,佐周有功,封于营丘,裔有穆公,以地为姓,是为丘氏。不入图,是以不信其实据也。后至云崖公,辅汉有功,官授司空,封于河南,始以地为郡,是为河南郡。迨至行恭公者,唐主聘讨高贼有功,封于天水,此又是以地为郡,是为天水郡者。两郡并传,乃为丘氏望族。
荣观各处族谱,镇平举人占,江西举人毓锟,平远岁贡嘉宾,暨白砂、蛟洋、中都等谱,世代参差,总说不一,皆不可以深信焉。观今太拔祠,俱说三五郎公在此开基,当曰是邱姓私祠。因子孙式微,难拒张、范二姓。道光五年,邀集邱氏一族,议建三五郎公之祠,若作开基事,属谬矣!至光绪五年,总理银和修整其祠,我房始入配享十四名。又查得继龙公之名字,诸先辈俱未说及,只有八郎公,现据万历二年筑造梅花落地,迎魂安葬,碑书:“八郎公之墓”矣。
后至崇祯五年,之麟、梦鲤、一炳公等皆是博学君子,创建杭南邱祠,立神主始祖八郎公,一世祖惟禄公。至咸丰四年,换过神主,则写始祖继龙公。至八月秋祭,镇平蕉生等来杭,痛责易名之错,三房经理无词可对,事成已久,将就而已。
据镇平等谱,继龙、从龙、梦龙又属旁支,恐其不确之故也。而继龙公之名字,从何而来,诸先贤达俱未曾述。查得嘉庆十九年创建丘氏总祠,不知何人写在神主,当时族众未曾深究,后人随其称也。今八郎公之名,无人称矣,况前辈之贤能,未必亚于后人之高见,亦未必胜前人以世代之相推其传也。较远以年数之相算其立也,在前可叹也哉。只得聊备数言,以待后来贤达者,再为考究。
清光绪己丑(1889年) 廿三世嗣裔 国荣撰
【注】此序作者国荣,上杭黄坑四三郎公派下六七郎公裔孙。他根据黄坑老谱,并走访了本县中都、白砂、蛟洋以及广东蕉岭、平远、江西兴国等地查阅了旧谱,写出了这篇资料,以供后来者考究:一,对于上祖源流一则(指八郎公之前),前人一概未述。二,继龙公名字,从何而来,诸先辈俱未述及。现据万历二年(1574年)筑造梅花落地,迎魂安葬,碑书:“八郎公之墓”。三,1636年上杭城南门建祠立神主始祖八郎公,至咸丰四年(1854)换过神主,则写始祖继龙公。只因当时未曾深究,后人随其称。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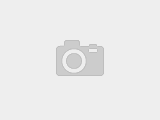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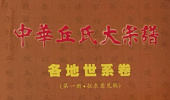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